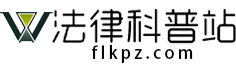違約金過高調整的認定程式?
我國的合同法對於違約金有著詳細而完整的規定,在合同交易過程中,違約金的調整一直是大家經常接觸的對問,而我國法律法規也具有對違約金過高調整和過低調整的司法認定程式,今天法律本站小編帶您瞭解違約金過高調整的程式。

一、違約金的性質分析
違約金是指由當事人約定或法律規定的,在一方當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時向另一方當事人支付的一筆金錢或其他給付。[①]違約金具有擔保債權實現、補償守約方所遭受的損失、懲罰違約行為的功能。
違約金包括賠償性違約金與懲罰性違約金。賠償性違約金是損害賠償額的預定;懲罰性違約金對債務不履行的制裁。[②]二者有如下區別:首先,功能不同。賠償性違約金的功能在於彌補一方違約後另一方所遭受的損失,使得守約方恢復到合同訂立前或合同如按約定履行時的狀態;懲罰性違約金的功能在於制裁違約行為。其次,與其他違約救濟措施的關係不同。賠償性違約金具有彌補損害賠償的功能,故債權人不得在違約金之外再請求強制履行或損害賠償;在懲罰性違約金的場合下,債權人除請求違約金外,更得請求強制履行主債務或請求損害賠償。第三,與實際損害的關係不同。賠償性違約金乃損害賠償額的預設,違約金應與實際損害額大致相當;懲罰性違約金,主要功能在於對違約方的懲罰,即使沒有損害發生當事人也可以請求支付違約金。
考察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立法,大陸法系認為違約金兼具補償性與懲罰性,英美法系嚴格區分違約金和罰金,強調合同關係是民事關係,當事人之間是平等的,因此不允許當事人之間實施懲罰,不允許當事人約定違約罰金。[③]
我國《合同法》第114條規定了違約金的性質,對於其理解學界有不同的觀點,有學者認為就114條第一款關於違約金的規定來看,立法者將違約金與損失賠償額的計算方法並列,表明違約金與損失賠償額的計算方法在性質上具有相似性。而且,第二款未區分違約金的性質,統一規定當違約金的數額過分高於損失時,需要對違約金進行調減。這一規定,使得懲罰性違約金喪失了其根本功能,並演變成了補償性違約金。從而使得懲罰性違約金只在名義上存在,而在實際上卻變成了損害賠償之預定。[④]
另有學者認為合同法上的違約金制度規定並沒有禁止懲罰性違約金,因此當事人之間約定的懲罰性違約金並不能因為其具有懲罰性而否定其效力,但是在對114條的理解上又存在分歧,一部分學者認為該條規定的違約金屬於賠償性違約金,即使第三款規定就遲延履行約定違約金可與履行債務並用,但此時的違約金在性質上也只是對遲延賠償的賠償額預定,仍屬於賠償性違約金。但是由於合同法奉行自願原則,當事人仍可以約定懲罰性違約金,如果無法確定當事人的約定系賠償性違約金還是懲罰性違約金,原則上推定為賠償性違約金[⑤]。
另一部分學者認為認為《合同法》第114條規定的違約金性質兼具補償性與懲罰性,並且以補償性違約金為主,懲罰性違約金為輔,筆者認同這一觀點。首先,114條強調“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於造成的損失的”,須“當事人請求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法院才可考慮是否予以適當減少,法院並不能依職權直接減少過高的違約金約定,因此如果當事人沒有請求予以適當減少,而該約定又沒有無效的情形,當事人也未主張撤銷、變更,那麼“過高”的違約金也可能被支付,此時違約金責任的承擔即體現了違約金的懲罰性。
其次,114條第三款規定“當事人就遲延履行約定違約金的,違約方支付違約金後,還應當履行債務”。遲延履行的違約方支付違約金後,仍要依約履行合同義務,此時違約金明顯具有懲罰性。最後,按照合同自由原則,依照我國合同法的規定,當事人可以約定無論是否造成實際損失均應支付違約金,類似約定並不因其具有懲罰性而無效,違約方應當向對方支付違約金。如此,違約金的支付就不以損害的發生為前提,即使沒有損害發生當事人也可以請求支付違約金,體現了違約金制裁違法行為的功能。
但是,114條第二款又統一規定對於過高的違約金當事人可以請求適當減少,避免違約金過分背離實際損失,而且116條關於定金條款與違約金條款的選擇適用及《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28條關於當事人請求增加違約金後不得請求對方賠償損失的規定,都強調了違約金的補償性。因此,整體來看我國合同法規定的違約金兼具補償性與懲罰性,但補償性為主,懲罰性為輔,這就決定了法院在調整過高的違約金時,要兼顧違約金的補償性與懲罰性。
二、違約金調整的法理依據
通過事先約定違約行為發生之後違約方可能承擔的違約責任,迫使債務人基於可能承擔的違約金的壓力竭力履行債務,從而促進履約行為。另一方面,一旦違約金的給付條件成就,違約方依照事先的約定承擔相應違約責任即可,合同雙方當事人不必再糾纏於損失的計算,有利於糾紛的快速解決。因此,法律尊重當事人在合意的基礎上達成的違約金條款,並認可其效力,不僅是私法自治原則的體現,也是效率價值的實現。如果司法隨意介入調整不僅不符合當事人的合意,也有悖於效率價值。但是現代民法基於民事主體具體人格的認識,基於社會公益的考量,不同程度地介入私主體自治的領域進行調整。之所以要對當事人約定的過高違約金進行調整,就是要通過消減超出實質正義範疇的不合理部分,防止地位優越的一方利用其強勢地位,通過約定過高的違約金條款獲取不正當利益,使違約金條款異化為一方壓榨另一方的工具。違約金過高司法調整的法理依據,決定了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在具體適用違約金調整規則時,應該衡平合同自由與合同正義的要求,合理把握公權力介入當事人自治的範圍;應當兼顧違約金的補償性與懲罰性,重視違約金損害賠償預定的屬性的同時,也要避免違約金擔保債權實現的功能被架空。
三、違約金過高的司法認定
《合同法》114規定只有違約金過高時,當事人方可請求予以適當減少,因此針對一方當事人的適當減少請求,前提是違約金的約定過高。
(一)損失範圍的確定
《合同法》第114條規定違約金過分高於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予以適當減少。判斷違約金是否過分高於造成的損失,首先就需要明確損失的具體範圍。《合同法》第113條第一款前段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損失賠償額應相當於因違約造成的損失,包括合同履行後可以獲得的利益”。通說認為,該規定確定了合同法上的完全賠償原則,即合同主體可以通過違約損害賠償達到如同合同全部適當履行時應達到的狀態。[⑥]114條第二款將違約金過高參照的損失表述為“造成的損失”,與113條一致,但是《合同法》解釋二第29條又表述為“以實際損失為基礎”,通說認為實際損失同信賴利益損失,即一方當事人由於信賴合同的有效性而遭受的損失,此時須使守約方恢復到如同合同未成立的狀態。很明顯信賴利益損失並不包括可得利益損失。
是不是可以認為違約金制度中的損失並不包括可得利益損失?對此,筆者認為,29條第一款要求法院參考“預期利益”裁判,可見司法解釋並沒有排除可得利益。因此,確定損失範圍時,亦應包括可得利益損失。此外,在確定損失範圍時,須注意可預見規則、損益相抵規則、過失相抵規則等相關規定對於損失範圍的限定。
如果違約行為並未造成損失,甚至守約方獲得的利益超過了其所遭受的損失,此時,當事人提出要求適當減少違約金,法院實際上無法在違約金與造成的損失之間建立對比關係,對於當事人的請求法院應該如何裁判?筆者認為,首先,應該判斷此類違約金條款是否存在無效及當事人是否針對性地提出撤銷、變更違約金條款的請求。還要尋找其他部門法對於一些特殊領域的違約金是否有強制性規定。其次,在舉證責任上應由主張予以減少的當事人承擔證明損失不存在的事實。(通說認為當事人約定違約金條款的目的之一就是避免損失的確定和計算,因此主張違約金責任的當事人只需證明違約行為發生即可,而不需證明損失是否實際發生及損失額的大小。)如果承擔舉證責任的當事人能夠證明且違約金在性質上屬補償性的(由於合同法違約金的性質以補償性為主,因此在當事人無特別約定的情形下應推定為補償性違約金),則可以免除。但是,如果當事人有諸如明確約定無論是否造成損失違約人都要在違約行為發生後支付違約金的懲罰性約定,此時,裁判者首先應考慮違約金約定是否有違合同正義,有乘人之危、顯失公平的嫌疑,否則法院應尊重當事人之間的約定。
(二)違約金過高的認定標準
《合同法》第114條第二款未區分違約金的性質,統一規定以違約金是否過分高於造成的損失為標準來認定當事人是否可以請求法院減少違約金。《合同法》解釋二第29條第一款則強調法院應當以實際損失為基礎,併兼顧合同的履行情況、當事人的過錯程度以及預期利益等綜合因素,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予以綜合衡量。29條第二款則為法院在一般情形下判斷違約金是否過分高於造成的損失提供了相對客觀的量化參考標準,即違約金高於造成的損失百分之三十。司法解釋將彈性與剛性規定相結合,為法院裁判過高違約金問題提供了妥當的方案。司法實踐中,面對錯綜複雜的法律關係,適用29條時,法官面臨的問題往往是如何正確適用第一款與第二款,如何理解以實際損失為基礎與兼顧其他因素之間的關係。
《合同法》解釋二第29條第二款為法院判斷違約金是否過分高於造成的提供了量化的參考標準即:“當超過造成損失30%”時,“一般可以認定”為過分高於損失。該款規定將違約金過高的認定標準與損失直接掛鉤,即一般情況下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系造成的損失1.3倍以上時,就可以認定為過高。百分之三十的量化標準考慮到了守約方難以證明的損失、非財產損失,兼顧了違約金的補償性與懲罰性適度,相對客觀的標準也減少了法官適用法律的隨意性,有利於同意裁判尺度。但是,如果一刀切地適用百分之三十的標準,則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一旦高於違約行為造成的損失的百分之三十,只要違約方通過反訴或者答辯的方式請求適當減少並且也能夠證明其主張,違約金就會被適當減少,造成的後果是當事人的意思自治空間被司法壓縮,司法裁判背離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使得違約金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落空,背離了合同自由原則。因此,在判斷違約金是否過高時,不宜一刀切地適用百分之三十的標準。筆者認為,確定了違約金高於造成的損失的百分之三十後,應當遵照司法解釋二的綜合標準,結合合同的履行情況、當事人是否故意違約、當前社會經濟形勢下民商事主體對於違約金懲罰性的接受程度、締約雙方的經濟能力等因素,綜合合同自由與合同正義,在充分尊重民事主體的自由意志的基礎上,認定當前的違約金是否有違公平原則,判斷合同是否具有特殊情形並且該類特殊情形足以使法院認為即使違約金高出造成損失的百分之三十也不構成過分高於損失。比如,經營者為了提高交易機會作出的假一賠十的承諾;旅遊合同中,旅行社為了吸引遊客以格式條款方式提供的高額違約金條款。
四、違約金調整的因素考量
(一)平衡當事人之間的利益
合同法第5條規定:“當事人之間應遵循公平原則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顯然,違約金高於造成的損失有違公平原則,但是法律之所以承認超出損失額度的一定比例的違約金的合法性,既是對於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同時也希望發揮違約金在擔保債權實現、懲罰違約行為的作用。因此在適當減少違約金時,一方面要充分尊重當事人在平等、自由協商並且準確確定的違約金金額,避免違約金混同於損害賠償金,失去擔保債權實現的功能。另一方面要通過司法調整,防止因為締約人的經濟地位、締約能力、對損失估計的不準確及社會經濟情況不可預計的變化,使得違約金過分高於違約行為造成的損失,從而導致非違約方獲得不正當的利益,違約方的財產狀況惡化喪失正當競爭條件的不公平結果出現。
(二)考慮各方當事人的過錯
在當事人無特別約定且法律無特別規定的情形下,合同法採取的是嚴格責任原則,即只要違約行為發生,即使債務人對於違約行為並無過錯,只要不存在免責事由,就不能免於承擔違約責任。違約金責任的成立並不以債務人有過錯為要件。但是違約金的功能之一是對違約行為的制裁,債務人是故意違約還是過失違約,或者並無過錯,直接決定著違約金制裁違約行為目的的實現程度。因此在調整違約金時,應考慮當事人的過錯。如果當事人系故意違約,這種故意違約行為或是出於需支付的違約金低於違約行為帶給其利益的衡量,又或是單純的不誠信行為,則在調整幅度方面要謹慎甚至是不予調整。對於過失違約行為產生的違約金與無過失行為產生的違約金在調整幅度上則要有所區別。在補償性違約金為主的前提下,通過調整幅度的差別,體現法律對於不同過錯程度的違約行為的制裁程度,有利於促進合同主體依照誠實信用原則行使權利、履行義務。
包括司法認定和調整細節。在認定過程中,法院一般考量依據綜合標準和具體標準,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全面認識應該遵循的原則和應當考慮的因素。在司法實踐中,克服違約金認定和調整的使用難題。